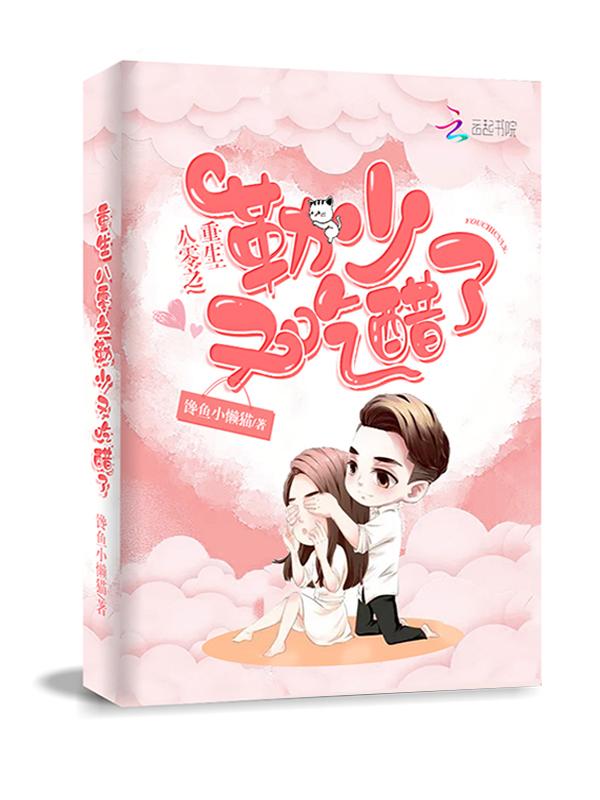零点看书>当我们建设大唐[贞观外交官] > 昔鸿恩二(第3页)
昔鸿恩二(第3页)
我回想起太子在朔日大朝上的轩昂气宇,今日在球场上的英姿勃发,心中难以反驳她的话。别说是太子自己,就算是旁观的臣工,也希望储君仪表堂堂、威风四方,而不是只能靠拐杖行走的人。
我叹了口气,道:“殿下的伤,实在……”
实在冤得很。
太子不愿意病重的母亲担心,因此隐瞒不发,谁能说他不是一番孝心?
可到头来,真正教娘娘放心不下的依旧是他的腿。天下间还有这样阴差阳错的弄巧成拙,城阳公主说,她想要去告诉圣人与娘娘,可太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。
太子仿佛赌着一口气似的,他不在乎自己的伤势,只在乎圣人对他的评价:“我想要为阿娘修建寺庙祈福,阿娘不接受。可惠褒说自己舍不得阿娘,不愿意到封地去,阿爷便破例留下他,还允许他在府里办文学馆。”
太子激动地问妹妹:“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文学馆?阿爷做亲王的时候,房公杜公全是文学馆的学士,那是文学馆吗?那是他的巢窠!为什么我做什么他都不喜欢,惠褒做什么都是好的?”
太子白天抓着杜荷倾诉,晚上杜荷回家了,他只剩下城阳公主。他没日没夜地忍受痛楚,城阳公主同样没日没夜地忍受他的宣泄:
“衡真,你知不知道惠褒③的封地有多少?他有二十二个州,吴王只有八个州,他凭什么那么多?④”
“衡真,你知不知道阿爷允许惠褒乘撵上殿④?舅公那样年迈,舅公都不坐撵,他为什么乘撵?”
“衡真,你知不知道阿爷常朝上骂了左仆射?左仆射见到惠褒没有行礼,阿爷气坏了,当着满朝的人说‘难道我儿子就不是天子的儿子,你怎么敢这样不尊重他’!⑤天可怜见,我倘若不对左仆射行礼,阿爷将我骂死了!”
“衡真,如今阿爷要惩治害我受伤的人,我偏要为他求情,我偏不要他死,教阿爷看看谁才是仁义的那一个!”
我听得头昏脑涨,仿佛真的有个人在我耳边咆哮。难以想象城阳公主是如何和这样的哥哥生活这些年的,这哪是哥哥,这不是一匹疯了的马么?
我苦着脸说:“因为太子是太子,魏王是魏王。圣人不会用太子的标准要求魏王,只会将他当成爱子来宠溺,这很难以理解么?”
“不难,可是我当时不到十岁,我也不理解,我也想不出反驳他的话。”公主道。
“那伤他的是什么人,可死了么?”
公主望着我的眼睛,道:“你猜不到?我以为你猜到了。”
我真的想不到,能是谁呢?
“你见过的。”公主说。
我见过的?逖之?
公主嘴角抽了抽:“你真敢想。”
魏王?
“……我们兄弟姊妹没那么畜生。”
左仆射?!
公主攥起披帛,挡着自己的脸:“要不你别想了,我害怕。”
敬时楼的钟磬前有司人等候,只待敲响散客的第一声。
轰隆隆的,西内苑群鸟惊飞,我在钟鸣的珑璁声中云腾脑海,不确定自己的猜测。
公主终于不再与我玩猜谜游戏,她轻轻地叹息一声,道:“你见过的,思摩将军的参将,夜闯礼部又自尽的突厥卫士,哥舒勒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