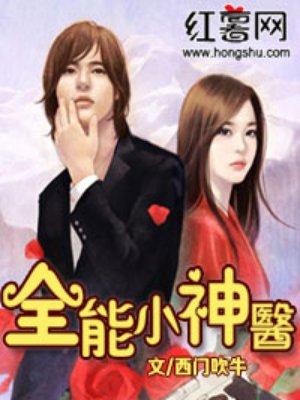零点看书>血色迷案录 > 第 76 章(第1页)
第 76 章(第1页)
夜色如墨,东宫之外,皇城之内,巡逻的禁军步伐稳健,其盔甲在月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。
此时,早已落锁的乾宁门,在寂静之中骤然敞开,发出沉重且悠长的吱呀声,打破了皇宫的宁静。
祁阳太子独自踏出乾宁门,月光倾泻在他肩头,为他披上一层银辉,然而却难掩他眉宇间凝聚的沉重与决绝。
他深知此行凶险万分,但为了东宫的安危,为了即将诞生的孩子,他别无选择。
养居殿内,灯火通明,靖文帝端坐于龙椅之上,手中紧握着奏折,看似已翻阅多时,实则未曾真正入眼。
他的眼神不时投向门外,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片刻之后,殿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。
靖文帝神情微微一动,他抬起头,目光穿过殿门,落在祁阳太子身上。
“父皇。”祁阳太子步入养居殿,行了一礼。
靖文帝的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,既有作为父亲的慈爱,也有帝王独有的深沉与威严。
此时,站立于靖文帝身旁的御前内侍缓缓上前,将手中的圣旨展开,高声宣读道:“奉天承运,皇帝诏曰:自古帝王继统,皆有天命所归,历数在躬,非可妄求。朕承祖宗鸿业,夙夜忧勤,期于天下太平,百姓安乐。然岁月不居,时序如流,朕年事已高,精力渐衰,深恐难以胜任国家之重托。
皇太子祁阳,秉性纯良,才德兼备,自幼受教于朕躬,勤学好问,深谙治国之道。其仁心仁术,广施恩泽于百姓,深得民心。今朕欲传神器于太子祁阳,以继正统,永保万世之基。钦此!”
祁阳太子闻此,身形微震,却只是低首沉默,未曾领旨谢恩。
靖文帝见状,示意御前内侍退下,继而起身走向祁阳太子,正色道:“你可知东宫今日之祸,皆因你一时之仁而起。若非你顾念手足之情,迟迟未作决断,诬陷你谋逆的奏章怎会铺满朝堂?”
“你孤身入宫,未携东宫六卫,虽意在向朕表明你无谋逆之心,欲以己身保东宫安宁。然此举在朕看来,实在愚不可及。”靖文帝语气中夹杂着责备与无奈,“时至今日,你虽无谋逆之意,但事态已非你所能掌控。”
靖文帝转身,从御案上取出一份奏章,递予祁阳太子,沉声言道:“东宫朋党之争中,太子太傅吕宗慎、东宫六卫大统领程其等六十三人皆涉其中,并有擅自调兵、图谋不轨之嫌。”
祁阳太子接过奏章,目光扫过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,心中一阵沉痛。他深知此皆东宫忠良,多年来功勋卓著,却因一己之仁而陷危境。
“父皇,吕太傅家三代忠良,程统领亦是屡建奇功…他们皆是忠诚之士,绝无二心,儿臣恳请父皇明鉴。”祁阳太子恳切地辩护道。
靖文帝却冷声责备道:“你虽无谋逆之心,然此六十三人图谋不轨,欲诱你行此悖逆之事。此等行径,岂可轻饶?朕若不严惩,何以正朝纲,荡奸邪?”
“不过你登基后,这些人如何处置,朕会留给你自行决断。”靖文帝语气稍缓,眼中闪过一丝深意,“只是朕已老矣,除你之外,无可信赖之人,若你对朕有所隐瞒,朕亦无能为力。”
养居殿内的气氛,因靖文帝之言而骤变沉重。
祁阳太子紧攥奏章,心中沉痛难抒。
突然,殿外御前内侍通报:“圣上,太子妃与秦王妃相继诞下皇孙,母女皆安。”
靖文帝听后,神色未变,但目光投向祁阳太子时,多了几分深意,他缓缓说道:“看来此乃天意!”
“父皇,稚子无辜,儿臣恳请父皇开恩…”祁阳太子急切恳求道。
靖文帝望着频频磕首求情的祁阳太子,终是轻叹一声,“孩子,心慈手软乃帝王之忌,你至今还未能明白这点,将来如何能掌管这天下?”
与此同时朱雀大道上,铁甲闪耀,禁军龙武卫步伐一致,穿越夜色,直奔东宫而去。
其大统领傅庭深,身披重甲,面容冷峻,于东宫门前勒马驻足,随即,禁军龙武卫迅速列阵,将东宫重重包围。
傅庭深翻身下马,迈着沉稳的步伐,直奔东宫大门。监门卫见状,急忙上前阻拦,但傅庭深只是轻轻一挥手,便有禁军龙武卫上前,将他们一一制服。
“奉皇上旨意,捉拿东宫逆贼!”傅庭深的声音冷硬而有力,回荡在东宫的高墙之间。
东宫六卫大统领程其紧握横刀,赫然拦在傅庭深身前,怒喝道:“谁敢踏入东宫半步!”
傅庭深冷笑一声,质问道:“身为东宫六卫之首,你本当恪尽职守,保护太子与东宫安宁,却私结朋党,藏匿叛逆,图谋不轨,你可知罪?”
“一派胡言,我程其一生忠于皇室,忠于东宫,何曾有过半点叛逆之心?倒是你们,公然诬陷太子殿下篡权谋逆,企图颠覆国本,才是罪大恶极!”
程其声如洪钟,眼神中满是不屈与愤怒,他身后的东宫卫士们也纷纷挺立,目光坚定,誓死捍卫东宫的尊严与清白。
傅庭深不愿多费唇舌,他高举手中令牌,示意身后禁军准备进攻。
程其见状,猛地挥刀向前,东宫卫士们亦纷纷抽出兵器,双方对峙,气氛紧张至极。
傅庭深目光如冰,冷然下令:“不必留情,东宫叛逆,格杀勿论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