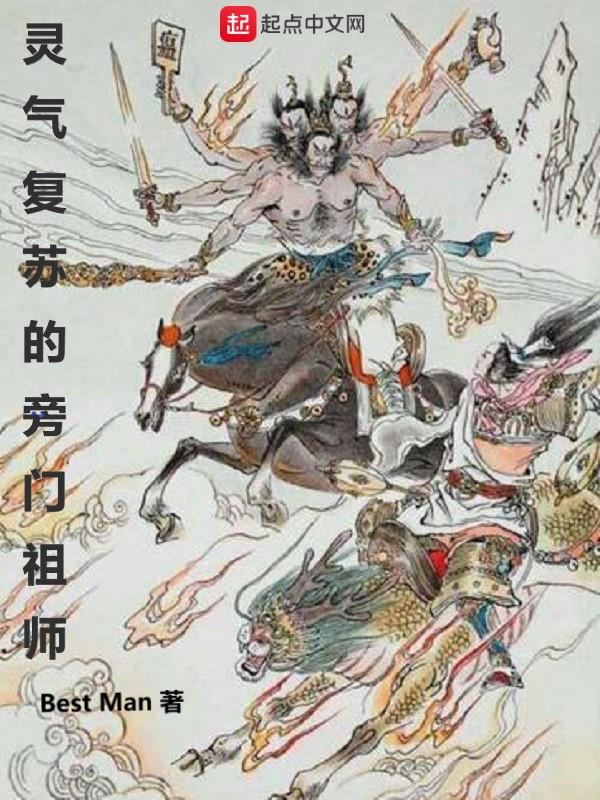零点看书>掌门怀孕,关我一个杂役什么事 > 第358章 祖先独孤夜星造化(第1页)
第358章 祖先独孤夜星造化(第1页)
“后辈独孤琉璃,参见祖先!”
回过神的独孤琉璃,当即拱手恭声道。
“独孤琉璃。。。”
九尾天狐虚影嘴巴微张,略显虚弱的低沉声音徐徐传出:“好孩子,吾等待万载千年,终于等来了一位返祖九尾天狐血脉的子嗣。”
“也不枉吾当初的孤掷一注了。。。”
“吾名独孤夜星,乃九尾天狐族独孤一脉脉首。”
林陌与独孤琉璃一听,顿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
九尾天狐独孤一脉脉首。。。
听上去,天妖狐族的这位来自九尾天狐族的祖先,似乎在。。。。。。
夜深了,山外的风卷着细雨敲打岩壁,像谁在轻轻叩门。那白发男子仍坐在火边,膝上落着的桃花已被他小心夹进《路人甲录》里,书页合拢时发出一声极轻的“啪”,仿佛是回应。孩子们早已睡熟,蜷缩在他身边,呼吸均匀而安稳。他伸手替最小的那个盖好破毯子,动作轻得如同拂去花瓣上的露水。
远处雷声低滚,却不是暴雨将至,而是某种更深沉的震动从地底传来。初圣山的陶罐群再次泛起微光,那光芒不再局限于山体,竟顺着地脉延展,如根须般蔓延向四方。启明城的赎心节木牌上,所有写下的愿望同时亮起,字迹浮空三寸,汇聚成一片柔和的星河。春风学堂的窗台上,那片曾飘入教室的桃花缓缓旋转,背面的小字悄然变化:
>“你讲得很好,谢谢你替我说下去。”
>
>“现在,轮到你们继续了。”
男孩??如今已是青年的先生??猛地抬头,窗外无风,可那片桃花却自行升空,绕着他飞了一圈,最终停在讲台正中,宛如一盏不灭的灯芯。
他知道,这不是结束。
这是交接。
同一时刻,西域绿洲的考古队正围坐在新涌出的泉眼旁。泉水清澈见底,映出的面孔越来越多,甚至包括那些早已逝去的人:老妪盘坐桃树下,皇帝背着竹篓走远,刑无赦站在学堂讲台前低头认错……还有那个白发男子,蹲在雪地里为孩子系鞋带的身影。
“这水……照的不是现在。”队长喃喃,“是人心动的那一刻。”
忽然,石碑再度裂开一道缝隙,新的文字浮现,不再是刻痕,而是由无数细小的光点拼成:
>“善不是洪流,是滴水。
>可当千万滴水同向而行,便成了江河。”
>
>“别问我为何坚持。
>问你自己??是否也曾为一人弯过腰?”
队员们沉默良久,有人摘下帽子,有人跪地轻触水面。一名年轻队员忽然起身,脱下外套盖在身旁冻僵的流浪狗身上,又掏出仅剩的干粮掰碎喂它。狗颤抖着舔他的手,他哭了:“我以前觉得,做好事要被人看见才算数……现在才知道,原来它一直看得见。”
话音未落,泉水骤然翻涌,一圈涟漪扩散开来,整片绿洲的沙土开始变软,草芽破土而出,短短片刻,荒漠竟现出绿意。井底深处,浮现出一行新字:
>“你看,信的人多了,奇迹就不再是奇迹。”
而在北境边关,那位曾为叛军首领的士兵如今已是戍边校尉。他每日清晨带着新兵巡逻,路过当年老兵咽气的地方,总会停下,放下一碗热粥,轻声道:“同志,今天也守住了。”
这日清晨,大雪封山,队伍行至半途突遇雪崩。巨量积雪轰然倾泻,眼看就要掩埋整支小队。千钧一发之际,一名新兵被乱石击倒,腿骨断裂,哀嚎不止。校尉二话不说,背起他便往高处冲,其余人紧随其后。可雪势太急,眼看追不上。
就在这时,风中传来一声低吟。
不是人声,也不是兽吼,而是一种近乎心跳的搏动,自远方隐隐传来。紧接着,大地微震,雪坡边缘竟浮现出一排脚印??不是当下留下,而是早已存在,像是被某种力量从时间里唤醒。每一步都精准落在承重最稳的位置,形成一条蜿蜒向上的安全路径。
“跟着脚印走!”校尉嘶吼。
众人依言而行,终于脱险。待回望时,那串脚印已在风雪中消散,仿佛从未出现。
当晚,他在营帐中写下日记:
>“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足迹。
>但我记得,十年前,有个人对我说:‘你在乎别人的时候,路就会自己长出来。’